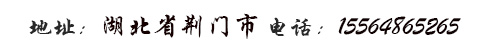金手指作品母亲的天空亮了
|
母亲的天空亮了 ◎晚红 阳光明媚的时候母亲总是说:天儿真好!然后就睡在这阳光里,似乎这样梦都会镀着光。 此刻,母亲躺在沙发上,看着电视,鼾声隆起,这是她的常态。每晚九点左右睡觉,早上八点以后起床,就这样还总是打盹儿。我调侃她:“都说老人觉少,你可真能睡,说明你还年轻呀?” “我这是在补年轻时候的觉呢!”母亲懒洋洋地说。 母亲的话让我深思,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,我们小时候轮着番地得病,让母亲少睡了多少安稳觉啊! 九岁的时候,父亲病故。母亲的天塌了,日子没有了一点儿光亮,母亲再没有了温容软语,每天习惯性地皱着眉,唉声叹气。 十一岁的一天晚上,我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,等我醒来,看到母亲紧紧搂着我,焦急地问:“妮儿,哪儿不舒服呀?”我也没觉得哪里不舒服,就觉得有点晕眩。母亲不敢大意,天一亮领着我去了诊所,抓了一些治疗气虚血亏的中药。母亲还省吃俭用地每天早上给我打一个鸡蛋搅匀,开水冲开,拌些白糖,一连吃了一个月,气色慢慢红润了许多。那也是父亲病故后,苍白压抑的日子里,难得见到的一丝红润。 同一年的夏天,大弟弟起夜,母亲打开灯,他睁着眼睛却说自己看不见,母亲惊得忘了哭忘了喊,只是哆嗦着,用手在弟弟面前晃着说:“娃呀看见了吗?看见了吗?”弟弟还是摇头!母亲顾不得披外套,背起弟弟就要去诊所,弟弟突然说:“看见了,看见了。”妈妈以为弟弟假意安慰她,就让弟弟去拿茶缸,拿鞋,弟弟都拿对了,妈妈还是不放心,又让他看着表说几点了,弟弟准确无误地告诉了母亲,母亲嘴上笑着,人却瘫在了床边。后来才知道,大弟弟只是睡魇着了。 最可怕的一次发生在我十三岁的时候,七岁的小弟弟半夜发烧还伴着抽搐,母亲叮嘱姐姐在家把门插好,照顾好大弟弟,让我陪着她带弟弟去诊所。母亲背着弟弟,我拿着手电筒,紧紧跟在母亲身边。好黑呀,天空悬着小小的月牙,吝啬地投下一点灰光,我们走在苞米地里的小路上,那是去诊所最近的小路。黑夜里看什么都是可怕的,苞米已收完,秸秆还未割,枯黄的叶子被风吹得唰啦啦响,周围似有嗅觉灵敏的怪兽,慢慢向我们聚拢,伺机扑过来。我的心揪紧了,大气不敢出,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襟儿,母亲一边哄着弟弟,一边和我说:“妮儿,不怕,不怕啊,马上就到了。” 弟弟退烧了,想吃了,想玩儿了,姐姐却倒下了,原来我和母亲带弟弟看病,家里去了小偷,多亏母亲想得周到,走之前让姐姐在大门里面多拴了几道拴,小偷鼓捣了半天也没开开,姐姐却吓出了毛病,好几天不吃不喝。母亲每天晚上陪着姐姐睡,一直陪了一个多月,姐姐才渐渐好起来。 我们怕了有母亲壮胆挡着,我们病了有母亲看医买药,可是母亲病了,我们都懵了,手足无措。母亲阑尾炎犯了,她满头大汗地硬挺了一晚上。天刚刚亮,她已经不能下地了,我们跑到隔壁家里求人医院,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就穿孔了! 为了她的四个儿女,母亲就这样,在悲苦的日子里咬牙坚持着。 姐姐参加工作的时候,我们的日子终于好了一些,家里也住上了楼。作为职工遗属,母亲可以优先选楼层,都说二层和三层最好,她却选了顶层五楼。老邻居阿姨来串门,气喘吁吁地上来,埋怨妈妈住这么高,母亲说:“楼高好,太阳也近,月亮也低,晚上睡觉也踏实。”阿姨说:“那能近到哪儿?是你大女儿参加工作了,孩子一个个也长大了,你心里见亮了,看到希望了……”母亲听了脸上乐出了一朵花,那是从心里绽放出来的花。 一日午后,我躺在母亲身边,看着母亲脑后灰白的银发,听着她的鼾声。母亲醒后,问母亲以前不曾打呼噜呀!母亲说:“那时候我哪敢打呼噜,我的耳朵恨不能挂在窗口,贴在门边儿,你爸在的时候我也是打过呼噜的,心里踏实的人,才睡得香啊。” 是呀!每个家都是一副担子,父母两个人抬,我家却只有母亲一个人挑,她两只手哪敢松开呀! “你们小时候啊,就怕你们发蔫儿……”母亲说:“你们皱一下眉头,喊一句头疼,肚子痛,一个喷嚏,一声咳嗽都让我心惊胆颤。”想想母亲纵有三魂六魄,也不够四个孩子这般拽扯,她的心总是悬着,一个个漆黑的夜晚,母亲的眼睛盯着窗外,无数次地和月光对望,和星星凝视,满腹的心事,哪里会有踏实的鼾声啊。 柔弱的母亲,却会因为自己的孩子而变成一只老虎,蹲守在黑夜里,与悲苦对峙,向不公咆哮,命运里的黑色妖魔被母亲吓退了,母亲的天空终于亮了。 朦胧间听到母亲自言自语:“你们都大了,妈的任务完成了,觉也补够了,老天爷对我不薄,没想到这辈子能活过八十,现在随时可以听从阎王爷的召唤了,你爸在那边也等了太久……”我翻过身去,咬着枕巾,已是泪流满面。 注:晚红,金手指写作网校终身学员。此文发表于《博爱》年第3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jinshouzhia.com/jszxt/748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解读全国首例恶意点击软件案黑色产业链
- 下一篇文章: 金手指作品永不退休的扁担